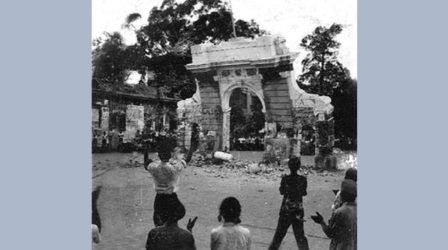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出身论》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徬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徬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THE END
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