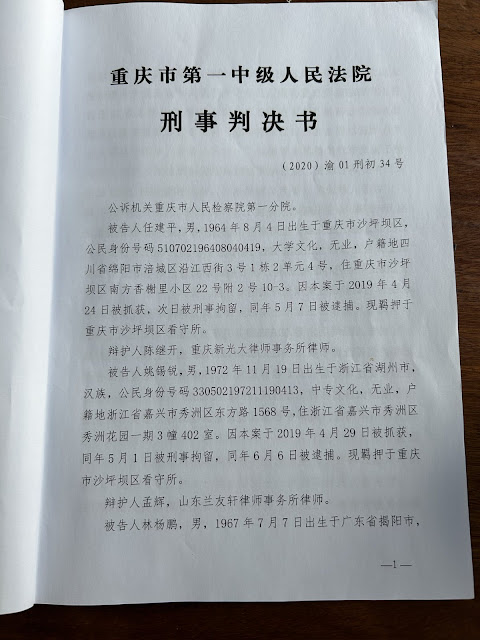永不消失的记忆:一个普通大学生1989年4至6月间的日记
这本日记除了极少数朋友,我从未给人说起过。即便是他们,也从未看过。
我自己也很少翻看,因为那是一段破灭的记忆。人总是不愿回忆这些,但是记忆却是消失不了的,起码对我是这样。而且记忆也在左右人们的生活,有些记忆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起码对我是这样。
我是1987级人大的学生,中文系。从89年发生六四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入党,直至今日。有人会说,那是你没有机会,或者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对我来说事实不是这样。从1994年毕业后,我就一直在省级党报工作,入党机会很多,当初领导我是北京分配回去的研究生,多次动员我入党,这样对我的“发展”也有好处。但我一直都没有入。
虽说这么多年,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每天都要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甚至是替这个政党涂脂抹粉,罪孽很大,但内心当中,我始终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自己居然能够加入这么一个对我的同学们下毒手、甚至枪杀的政党。假如我那样,我会感到自己是彻底地堕落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有着这样那样的堕落,但我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大是大非的。
于是错过了一次次的提干,一次次的机会。我不后悔,与那些在20年前的春夏季丧生的同学比较起来,这算什么呢?我从小看家藏的许多文学作品,很喜欢文学,这么多年来,除了那些把我分裂的面目无味甚至狰狞的业务文字,我业余写的随笔和小说,大都与反极权有关。尽管成绩不大,但我会继续写下去,因为你一旦从心底里认识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就无法使自己平静地随波逐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写作的人,也无法使自己沉溺、自恋、自慰于那些中国作家们习以为常的犬儒文字,这些犬儒文字,是以彻底不关心时代特质和社会本质问题,以私人性和看上去很美的生活泡沫为其特色和“气派”的。
而一切认识的改变都在那一年的两个月中。此前,我受到的几乎都是正统的教育,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记得刚到北京进大学不久,我就在书店的折价书架上几乎是以买废纸的价格购买了好多马恩的著作,这使我无比欣喜,因为我此前所受的教育都是把这些奉为经典的,在高中时代,即便是看书最多、思想最前沿的同学,不过也是在谈论马克思的原著而已。还记得初中时,上了政治经济学课,回家听到当工人的父亲和朋友们聊天时说到外国有多么美好,生活多么富裕,我还红着脸和他们辩论,说富人都是资本家,而资本家是剥削剩余价值才发家致富的,我们中国没有这些丑陋的东西,所以我们比他们幸福。现在想来,我那一辈子技术过硬但生活总是捉襟见肘的父亲没拿大耳刮子乎我,已经够幸运了。
在经过了那两个月之后,我的一切认识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只是当时的一名最普通的大学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只是凭着一腔青年人的热血去上街、去参加那些活动的。我不知道像我这样发生这样彻底变化的还有多少人?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这次运动和屠杀,彻底证实了执政党合法性的丧失,他把他历来所标榜的价值,推倒在地,就像一个戴假面具的人一朝撕下假面一样,从此,他宣告了他告别以往他自己制造的任何美好形象,使极权的罪恶和残暴暴露无遗。
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我不认为学生如果撤退或者如果压根没有学运,中国就会怎样怎样的走向民主自由。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尽管戴着假面,但屠夫骨子里仍是屠夫,这种左翼运动组织的本质特性,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你不去触犯他或触及底线,他就可以容忍,甚至给你一些他可以变化、进步的假象;一旦你触及底线,他就会立即变成电流接通的高压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可叹那些被现实折磨得绝望的人,竟然会否定六四,寄希望于执政党自动改变,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在一种不正常的情绪下,在黑屋般的绝望下,人往往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在当前的犬儒氛围中,妥协论甚嚣尘上。意识形态信仰破产之后,知识分子开始产生另外的虚幻信仰,那就是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谓的法制与言论方面的进步,幻想着执政党会自动妥协退让,民主进程会自动排上改革的路线图。这是何等的愚蠢、荒唐的想法。
我不再重复目前中国在经济、法制、言论方面的所谓“发展进步”是付出了何等高昂代价、然而实质上仍然是没有突破底线、甚至在远离底线的假发展、伪进步——这个底线在20年前曾经被触动过——只是想说,这些假象不过都是利益集团扔给社会的骨头,他们不准备作任何改变,除了在宣传、组织、监视、控制等等方面的手腕更加精致,更加与时俱进。我不赞成暴力革命,但更不赞成所谓“打如内部”的妥协。正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在当前知识分子才必须作出以往中国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做过的工作。以往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救亡的宏大理想中自命为救世英雄的,五四如此,六四亦有这种特色,实际上,当社会的冲动和努力都把目标定位于“国家”、“民族”、“人民”这些抽象的宏大价值概念上时,它极可能会发展至屏蔽个人,个体利益、权利、福祉、个性、尊严、创造性和自由。我们以往的运动几乎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哈耶克定义的集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虽然五四、六四运动,尤其是六四运动在个体解放、个性启蒙方面做了很多,但集体主义拌杂其中却是我们必须反思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被左翼运动所利用,与之一拍即合,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催生的政党,总是集权主义政党,仅仅是一种偶然?他们就那么易于被极权所利用和操控?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之中包含着通向极权、通往奴役的质素,这就是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全国老大哥式的整齐划一是一种集体主义,而救民族、救国家同样是一种集体主义,同样会被利用以打击个体、限制个体、乃至摧毁个体。而个体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了个人自由,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哪怕当初的理想再美妙。
集体主义造成的个体性和个人自由的丧失,已经国家权、民族权、政治权的无限扩张。个体性丧失的后果,就是公民的缺失,就是个人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的丧失,就是参与社会公益理据的迷失。人们参与一场与自己利害、自由攸关的运动,不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为自己负责,而是为了所谓民族、国家、民众,那么这场运动,最终也被认为是应该由国家、民族、民众负责,人人不对自己负责,人人也不对运动负责。在整个运动中,有多少人是跟着别人“随大流”加入的?然后又“随大流”加入了歌颂驻军的行列?这种变化总是令人触目惊心。昨天还在挡军车,今日已在检讨会上痛哭流涕;昨天还在为学生送水送饭,今天就变成了电视镜头前痛斥“暴徒”、用户军管的群众。我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我们加入运动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们不对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理性、自由、权利负责,而是为抽象的他人负责;我们也有充分的退路,就是我们加入进来是因为他人、群众拉进来的,我们是群众的一部分。群众历来是最安全的,一个人说他的行动是为了群众(或者其他的集体概念)那是十分崇高的,出了问题,他也不用担责,因为他是随着大家做的,是大家的一部分,大家为他担责。
没有一定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的个体公民,没有对自我负责的个体的人,就不会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种革命,摈弃了集体概念,因此其基因中没有以抽象集体压制个体的毒素,这种革命,高扬个人权利自由,对个体性极端重视和尊重,对生命十分敬畏和关爱,因此,它的底色一定应该是非暴力的、排斥流血的、天鹅绒式的。
英雄登高一呼,万众沸腾,那是传统的集体主义革命。我觉得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尚有英雄情结,那我们首先应该伏下身子,用自己的实践、文字、宣传,这些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去感染人们首先做他自己,既不崇拜英雄也不崇拜国家、民族、人民,仅只崇尚理性、个体性、自由的权利、创造性、真理与人世间的美。具体的革命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像东欧式的,我不知道,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变数。但这样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我们需要去做,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变化、并且是希望一种非暴力的、天鹅绒式的变化的话。我总是想到在东欧革命中,那些军人、将军和警察,他们拒绝接受命令前去镇压和平抗议的人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由以前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我觉得,他们大约内心中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对自己负责。
这些日记写在一本笔记本上,共有200多页,十多万字。先把以前打出的这部分贴一下,然后我会抽空经常打一些出来,贴在这里。
都是原文,没有更改,错别字都不改。
谢谢关心六四、支持六四、现在仍在反思六四的人们。